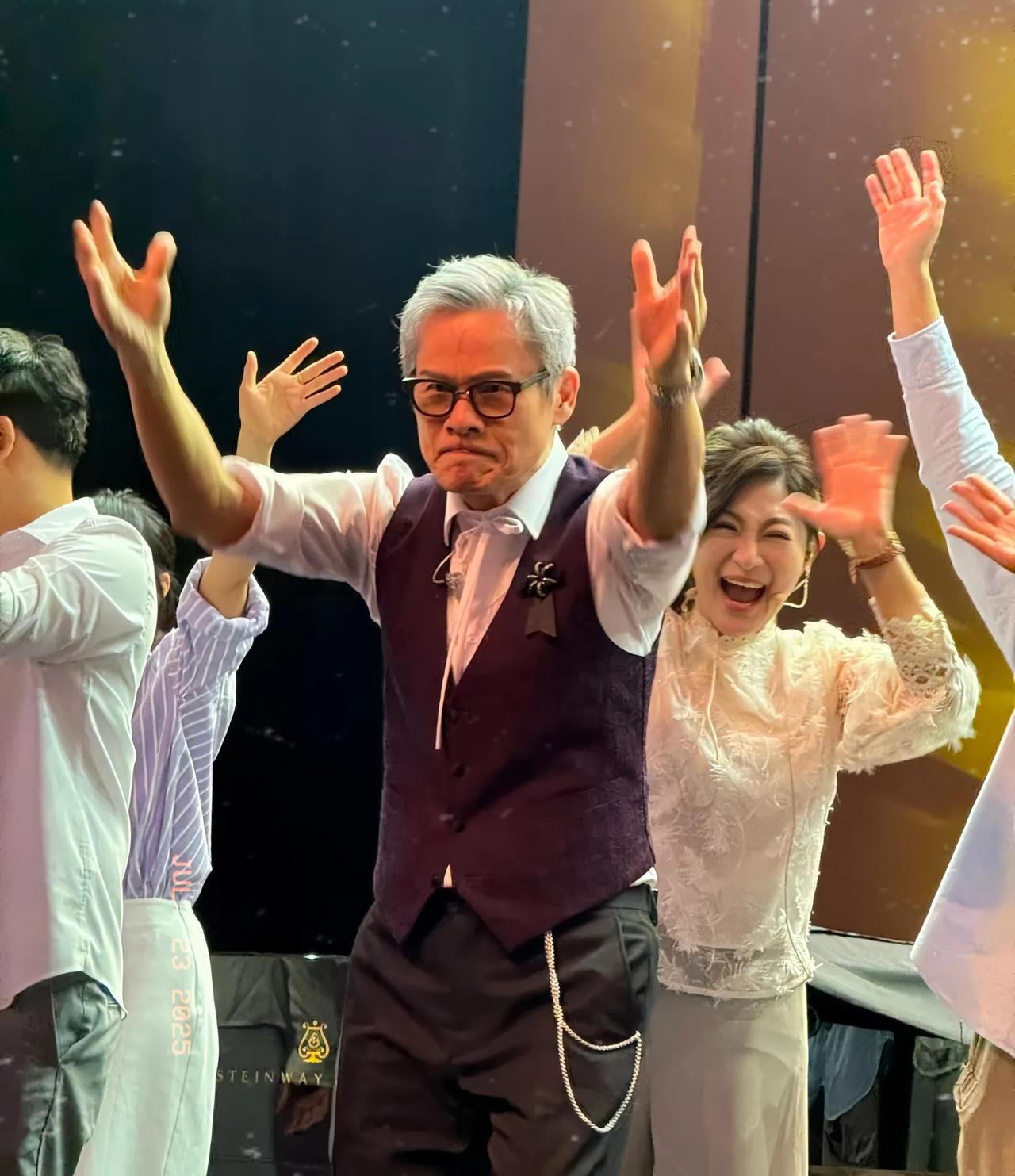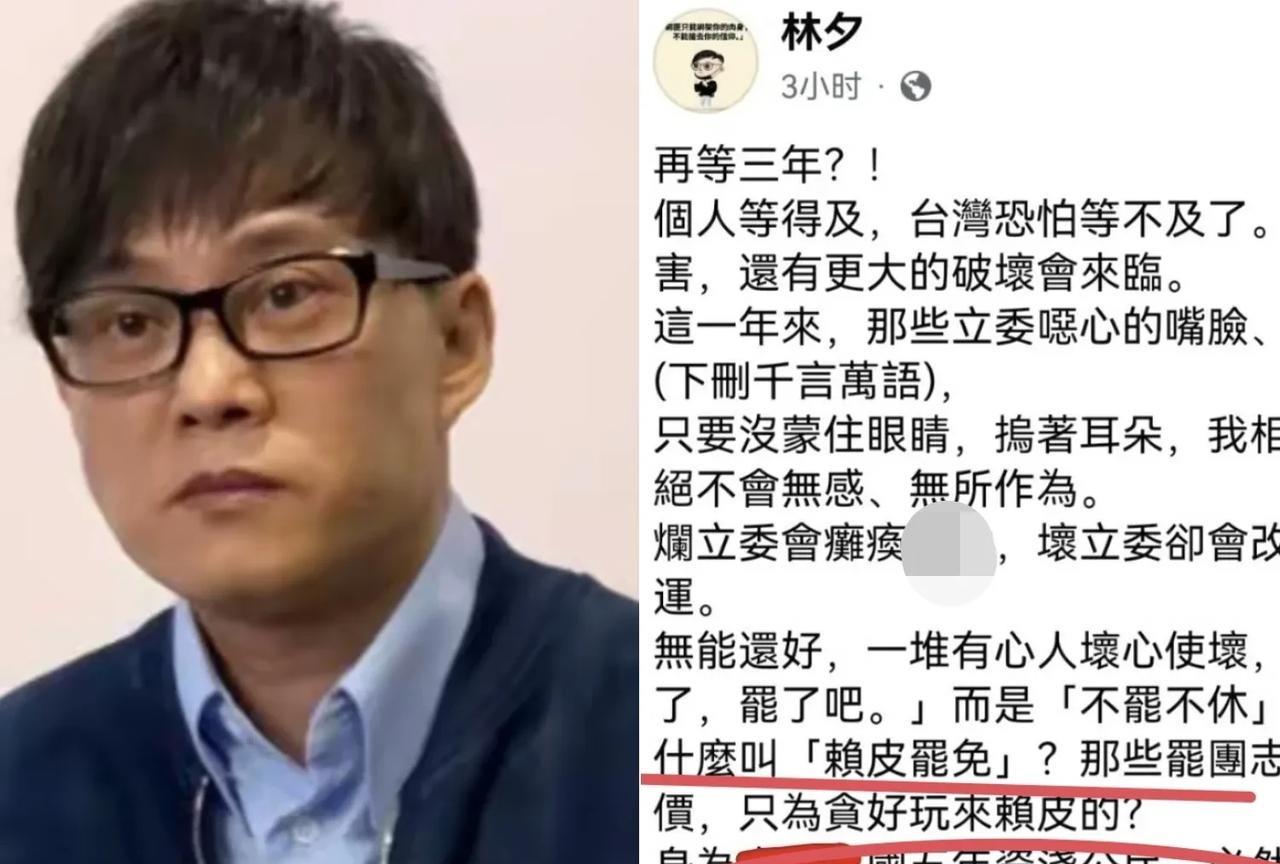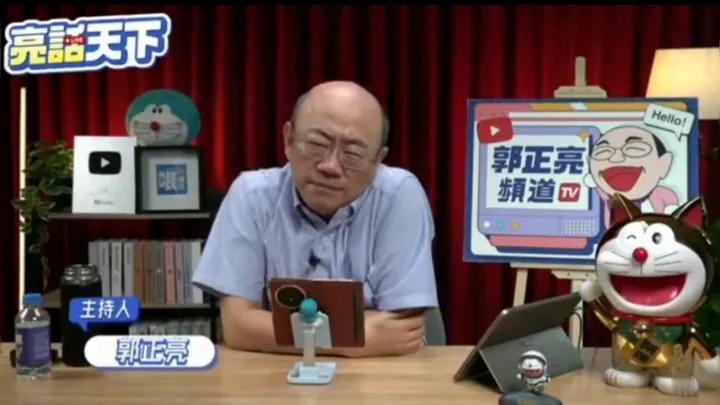1990年,李立群从台湾回到大陆,找到了同父异母的大哥,见到大哥家一贫如洗,他拿出三笔钱说:“哥,这钱我已经帮你想好花哪儿了,别拒绝”。 1990年夏天,李立群踏上了一趟不属于舞台、不属于荧幕的旅程,这一路没有观众,没有剧本,也没有排练,车窗外的风吹过黄土地,一路颠簸,他手里握着父亲递给他的纸条,上面写着一个地址,河南孟州的某个村子,他知道,这趟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父亲放不下的牵挂。 李立群出生在台湾新竹,家中并不富裕,父亲是从大陆随国民党迁台的老兵,母亲来自北京,他从小在台北眷村长大,家里排行最小,两个姐姐疼他,父母对他也不苛刻,小时候,经常听父亲在饭后提起大陆的往事,说得最多的,便是那位留在河南的长子,那个名字,李立群记了几十年,父亲形容得不多,只说当年战乱,走得太急,一别就是一生。 在台湾,李立群靠演技打出了名堂,从华视训练班出身,舞台剧、电视剧、综艺节目一路走来,凭借《卿须怜我我怜卿》拿了金钟奖最佳男演员,他演戏灵动,能说国语、台语、还有点河南腔,角色不分高低,演什么像什么,之后几年,他陆续参与了赖声川的舞台剧,还投身大陆影视圈,留下不少经典角色,但这些都和那年夏天的旅程无关。 那一年,台湾刚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,父亲已经年迈,身体也大不如前,某天,他把一张纸递给李立群,说:“你去看看吧,”没有多说,表情也平静,像是等了几十年,终于等来了一点机会,李立群看着那张纸,知道自己得走一趟。 河南的天气闷热,村子在地图上都难找,车子停在镇上,他背着包走了几公里土路,一路尽是麦田和泥路,村子的房子多是土坯建的,低矮、破旧,有些屋顶甚至塌了一角,他按着地址走进一个院落,看到那房子几乎没有门窗,墙皮脱落,院里堆着几根用来烧火的柴,就是这里,父亲的另一个儿子住的地方。 李建宇的生活和李立群截然不同,他靠种地、打零工维持生计,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,也没有电器,家里暗得像洞穴,墙角堆着一些农具和干草,他四十多岁,皮肤晒得发黑,衣服上缝着层层补丁,见到李立群,两人都愣了一下,没有寒暄,没有眼泪,只是站着,彼此打量,像是从镜中看到另一个版本的自己。 李立群没有停留太久,在屋里坐了一会儿,把随身带来的三叠钞票放在桌上,这是他提前准备好的,他知道,大哥的生活太艰难,靠自己翻身几乎不可能,第一笔钱用来还债,村里人说李建宇欠了不少账,都是为了种地、修房子借的,第二笔钱是修房子用的,那屋子实在不能住人,连个像样的屋顶都没有,第三笔钱,他想让大哥做点小生意,哪怕只是个加工农具的小作坊,也能养家糊口。 钱留下后,他没有马上离开,他在村子里住了几天,帮着搬砖、运木头、修墙,村里人都来围观,有人认出他是电视上那个演员,但更多人只是好奇这个穿着干净、说话带台湾口音的男人,孩子们在门口张望,老人们在巷口议论,李建宇起初拘谨,后来也慢慢放开,开始主动安排手头的事,把钱用在刀刃上。 还债是第一件事,他带着账本,一家一家登门,把借的钱按数还上,村里人都说他变了,走路都挺直了不少,随后他请来泥瓦匠,把旧房子推倒,重新起了个砖瓦房,新屋子不大,但结实、透气,还有了窗户,院子里种上了树,墙上刷了白灰,屋顶装了雨水槽,整个家看起来清爽了许多。 第三笔钱,他和几个村民合伙开了个小作坊,买了碾米机,也做些简单的农具,一开始没什么生意,但靠着乡亲们的帮衬,慢慢也做出点模样,他成了村里第一个能稳定挣到钱的人,村民们说他命好,碰上个有出息的弟弟。 李立群回到台湾后,继续拍戏,但这事在他心里留下了位置,从此每年,他都抽空回河南看看,带些衣物、药品、孩子的书本,他没有大张旗鼓,也不摆架子,就像普通人回家探亲一样,兄弟俩的关系也越来越近,从最初的生疏,到后来无话不谈,李建宇也逐渐放下了对父亲的怨,说到底,父亲走的时候,他不过是个婴儿,怪不了谁。 这段经历对李立群影响很大,他说过,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决定,每次提起大哥,他都认真而温和,甚至在拍戏时,他会带些河南口音的语调进去,说那是对家乡的纪念,他没把这件事当成施舍,而是当作一次家庭的修复,他知道,两岸的分离让很多家庭支离破碎,而他,能做的,就是把那一块拼回来。